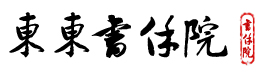
十六、一个人的传承
时间:2012/7/9 作者;东东书保院
一个人的传承
李广华 贺宇红
小作坊牵手“国字号”
若是没有人引领,光凭摸,找到浙江省宁波市奉化袁师傅的造纸坊还真不容易。满山翠竹,掩映着乡间公路,袁师傅的家就坐落在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边,沿河岸可以看到大缸、烧锅、料池等。他的家和作坊连在一起,算不上像样的房舍,倒像是棚户搭建的。家中湿漉漉的,滤池、捣浆桶、抄纸槽,杂乱地分布,捣浆的石臼里戳着碗口粗的木槌,斑驳老旧,散发着原始的气息,他的手工纸就是在这杂乱的环境里一张张地抄造出来的。
老袁今年74岁,造了一辈子纸。他出现在人们视野之前,一个难题曾困扰着国内众多的知名图书馆和博物馆,其中也包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那便是修复古籍,找不到相应的用纸。
外行人不大关注,其实,古籍娇贵得像个“贵妇人”,既受不了风吹雨淋,又耐不住冷热潮湿。娇嫩的“皮肤”遇到霉变、虫蛀、污渍、水渍、焦脆、粘连等伤害,身价就会大打折扣。而藏于深闺秘阁,“贵妇人”又多有疾病缠身,仅据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1976年对馆藏8万卷善本普查显示:脱线的有2427册、虫伤的3017册、水迹霉变的574册,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给“贵妇人”疗伤,用现代纸,不符合“修旧如旧”的古籍修复保护要求;用古代纸,哪里去找?
受纸困扰,宁波天一阁也曾向兄弟单位求助过,但哪家得到好纸都视为宝贝。古纸,真可谓洛阳纸贵。无奈,他们只好另辟蹊径,跑到浙江、福建、广东、安徽的一些造纸厂考察寻找,可工业化流水线下的产品,并不符合古籍修复要求。
天一阁博物馆李大东副研究员分析,宋以后,浙江是中国造纸的中心,而奉化有着悠久的造纸历史。他摸到当地一问,村民们说:“现在造纸不赚钱,没人造了,有家姓袁的好像造些。”1997年4月的一天,李大东敲响袁师傅家门时,眼前的景象多少有些让他失望:简陋的设备,布满了灰尘,脚下的池槽干枯见底,作坊已近倒闭。一打听,原来是老袁接过一个外贸单子,可生产一半,对方撕毁了合同,他购进的5万公斤竹料黏到手上,赔了血本。李大东查看一圈,见工艺设施和生产原料很原始,具备生产古籍用纸的条件,他眼前似乎呈现出一线希望。
在袁师傅手上,造过寿纸、印刷纸、窗户纸等多种用纸,最能体现他技术水平的是贴金箔用的乌金纸,但这和修复古籍用纸还有很大区别。老袁人很随和,对李大东的想法,也很有兴趣。专家提出的纸张薄厚、颜色、配方和纤维构成等,尽管改变很大,都一一答应下来。为了让他增加感性认识,李大东还邀请他到天一阁翻阅馆藏古籍,给他讲古籍用纸的特点,并鼓励他说:“你造的纸用在古籍修复上,也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作贡献!”听了这话,老袁一扫往日的沮丧,露出难得的笑容。在李大东的指导下,原料调配了不知多少次,配方改了又改,前后经过上百次试验,老袁终于拿出了修复古籍的专业纸。他同时还研制出了一种国内也是少见的,具有苦涩味道,能防虫,可用来修复古籍又适合画画的苦竹纸。
奉化能生产修复古籍的纸,立刻引来国内外的众多专家。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全国纸质类文物保护专家奚三彩专程来到当地,翻着老袁的纸高兴地说:“我走了好些地方,还是这里的工艺古朴、完整,造出的纸最好。”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两次到当地考察,认为这里的纸适合古籍修复,她还把纸推荐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副馆长宫爱东考察后当场定下10万张。
四处透风的小作坊,造出了稀罕之物,令专家们不得不另眼相看,他们也赋予老袁的纸一个新称谓——东东纸。而令老袁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小作坊连接上了天南海北的“大机构”: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西大学图书馆等地的专家先后来考察,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东东纸”。
原生态的现实解读
“吧唧”、“吧唧”,老袁光着脚,用力地蹦着石臼里沤好的竹料。石臼裂着一道裂隙,斑斑驳驳,腰间还缠着一道铁丝。他将竹料碾碎成糨糊状,再放到滤池中过滤,然后用无杂质的竹浆去抄纸……
每年的五月底六月初,天气温热,是造纸进料的最佳时间。已生长一个月左右的嫩竹,是理想的原料,此时笋壳刚刚剥落,叶子还没长出,不软不硬,纤维多,纯净度高。用石灰粉,在沤池中泡两个月,使其完全腐烂,之后用锅煮一天一夜,熟透后再装回缸,在太阳底下晒,进行自然发酵。夏天需一个月左右,冬天要几个月。原料沤差不多了,要装进粗布袋挤干,再捣踏、漂白、打浆、过滤、抄纸、压榨、晒纸,经过这一系列的程序,老袁的纸才能造出来。细想想,生产一张棠云纸要几个月时间,光程序就有72道之多。
东东纸的秘籍主要在于它的配方,除上好的苦竹、桑树皮、棉麻等必不可少的原料外,还要有野生猕猴桃藤、冷饭包藤、豆腐渣树叶等辅料,这些配方并没有文字记载,全凭老袁自己摸索。
专家们也到过许多现代的造纸厂,轰隆隆的机声下生产出的大卷纸,无一不是用现代配方调和出来的,粗糙、酸性和脆硬无法用在古籍上。而看了老袁的配方,仿佛让他们回到几百年前,看到那布满灰尘的古籍背后曾经有过的生产链条。
古法、古方,造“古纸”,这一切也是在现代化空气笼罩下,在老袁简陋的作坊里完成的。老袁的一招一式,自然会引来人们异样的目光。美国普利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刊主编罗南熙到老袁家参观后大为惊讶,他万万没想到在现代化的今天,在浙江宁波还能看到如此原生态的作坊,他感慨说:“这里的工艺比较传统,用植物原料生产,这么古朴的方式很难见到了,我看完简直都不想走了。”
老袁只有一亩多山地,因造纸需要,他种满了毛竹,但还远远不够,更多的原料还要向人家买,仅此一项就是不小的开销,他要确保每年30万张纸的原料供应。
爱较真儿是老袁的一大特点,配方虽然密,但他从不做手脚,从不用现代药水代替原始配方。所需的猕猴桃藤等原料一定要新鲜,否则便会失去药性。野生植物,近处的山林里已经很难觅到,一定要到深山里去找。蜂蛰蛇咬,几乎每年都要遇到几次。幸好,他掌握了排毒方法,否则老命早就搭上去了。
涓涓河水从作坊边静静地流过,岸边摆着二十几口大缸,既显得原始,也有些杂乱。老袁一边从沤池里捞着竹料,一边对我们说:“我专门设几口大缸过滤河水,不能直接排放到河里去,我也要注意环境啊。”这一点,他的小作坊又跳出了原始的境界。
最后的作坊主
据明嘉靖十一年的《奉化县图志》记载,“明永乐年间奉化上贡朝廷日历黄纸二千七百五十张、白纸七万一千张。”奉化自古为纸张的主要产地。600年间,在这个不大的区域内,产生过多少有名望的造纸能手,恐怕今天没人能说得清楚,造纸给奉化人带来过怎样的荣耀与辛酸,也没人能讲明白。
当地的一份家谱记载:明朝时,奉化江家的祖上在朝廷做大官,因被人陷害,告老还乡。老先生由于在江西等地任过职,熟悉那里的造纸技术,返乡后遂以造纸为业,打发时光,排解心中忧愤。江家太公夫妻恩爱,共同劳作,配合默契。一段时间下来,纸越造越好,成了远近闻名的抢手货。想到官场险恶,再看看这乡野和谐的生活,老太公感慨道:“日日进分,夜夜钻床,人生佳境,不过如此。”
到解放前,奉化造纸作坊有300多家。每到秋季,造纸的乡亲们总会凑些钱,请来戏班子,在庙里做蔡伦戏,纪念这位造纸始祖,感激先人给他们带来的养家糊口技艺。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如今,整个地区就袁师傅一个人还在和造纸打交道,他成了最后的一名守望者。
诚实本分的老袁,一生几乎没离开过造纸这一老行当。他17岁学徒,后进当地造纸社。大跃进那年,他进了地方国营造纸厂,成了一名造纸工人。几十年后又被下放回生产队,重新做起了农民,继续造纸。1982年干个体时,还是操老本行,产品销往土特产公司。给老袁心里留下阴影的一件事,是1994年日本客商通过土特产公司订购的80万张纸,突然提出不要了,他进的原料大量积压,赔了很多钱。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作坊要倒闭,不免心如刀绞,可他又没有能力挽回这颓废的残局。恰在此时,天一阁的人找上门来。
老袁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从小耳濡目染,孩子们也都对造纸很在行,但眼下没人愿意干这又苦又累、收入微薄的活计。三个儿子在外面打工、小女儿袁某和丈夫江某心疼爸爸,过来帮他造纸。袁某说:“老爸对造纸有感情,考虑他年岁大了,我们过来陪他一起做。”有时,交齐一批货,要很长的周期,年初定的价格,到年底交货时,原料价格就涨了很多。孩子们让他也相应地涨点价,不能赔本干,可老袁就是不肯,说当初定好的怎么能随便涨呢?
虽然年逾古稀,但老袁还是像个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停不下来。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忙到晚上五六点。有了女儿、女婿作帮手,他可以松口气了,像抄纸这样的累活,多数由女婿来承担,可有时他还是要亲自上手。
老袁抄纸像变魔术一样,一双粗糙的手,端起细密的竹帘,沾进浆槽,前后一晃,帘子出水,一层纸浆挂于帘上。慢慢揭开,由浆为物,一张湿漉漉的、有些透明状的纸呈现在眼前,神奇得让人有些诧异。这看似简单的劳作程序,并非易事,干长了,腰椎脊椎都会落下毛病,老袁也没能逃脱。
烘纸是最后一道关口,抄好的纸要拿到烘箱去烘干。所谓烘箱,其实就是能加热保暖的小土方子,里面有火墙,刚抄出的纸要糊到火墙上烤干。夏天外面摄氏40多度,里面简直就是蒸笼,烤得人跟水洗过似的。读起抄纸和烘纸,老袁概括为:“六个月大,六个月小。”他说夏天抄纸舒服,冬天烘纸舒服。夏季天热,在阴凉下与水打交道,总是感到爽快些;冬季天寒,钻进烘箱里,暖呼呼的,活儿当然好干。反过来,也有一半的时间是活受罪。老袁的乐趣,或许就在这一“冷”一“热”间。吃苦和享乐,他都要面对。
忙过一阵,他喜欢坐下来喝几口自家酿制的米酒,并常常得意地对孩子们说:“天一阁、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一些重要古籍收藏保护单位都用上我的纸,我既对不可再生的古籍保护作了些贡献,还为政府纳了税呢。”这个时候,满脸胡楂的老袁显得最惬意。
中国文物报
2008年5月7日
上一遍:十五、浅谈古籍修复的若干要点
下一遍:十七、深居天一阁的古书修复师李大东
欢迎访问东东书保院 Copyright ©2008-2020 东东书保院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05004270号-1
友情链接:中国废品网
